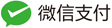燕京新語丨劍指長天,心向逍遙,原創話劇《鄧世昌》譜寫一曲英雄浪漫悲歌
巨輪傾倒,海水刺骨,王雷飾演的鄧世昌一襲紅袍,身后再回望,依然熱血難涼……原創話劇《鄧世昌》以第一視角的倒敘展開。雖然這是個所有人都知道結局的故事,主創卻用真情填補了歷史的縫隙,當鄧世昌隨著強國之寄望一同沒入黃海之時,觀眾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浪漫主義的悲壯。即日至5月4日,國家大劇院原創話劇《鄧世昌》在京首演。

舞臺上近500平方米的冰屏,將黃海海戰的炮彈、浪花、以及致遠艦飛速前進的畫面打造出“裸眼3D”的視效。矩陣式的龍骨與平行的透明屏交疊,承載了北洋水師的現實場景,又給予郵輪、宮殿、鄧家等場景的靈動轉換。“致遠號”作為引子,象征著亂世暌隔的歷史場景,在無邊深海光影中,生動地詮釋著清朝人物群像。
看《鄧世昌》,就不得不提起導演王筱頔上一部和國家大劇院合作的歷史人物話劇《林則徐》。
《林則徐》舞臺之上那塊印有中華版圖的斜坡讓人印象深刻,與之空曠簡約相比,《鄧世昌》的舞臺更滿,透明屏切割成大船的局部,以不同的層高劃分出不同的演區,但兩部劇一以貫之的是舞臺風格有厚重的歷史感,賦予觀眾想象空間。如果說《林則徐》提出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讓國人睜眼看世界,《鄧世昌》所處的年代,李鴻章已經進行了30多年洋務運動,誕生了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。鄧世昌等一批有著報國之志的年輕人也曾充滿希望,好像看到了能夠改變屈辱國運的曙光。
腐朽之氣與浩然之氣的強烈沖突,構成了《鄧世昌》的主線。慈禧一心只想為自己籌辦六十華誕,北洋水師在六年的時光里慢慢從亮色變得黯淡。舞臺上的大船,不僅是致遠艦,也是大廈將傾的清廷。面孔涂得煞白的慈禧,也在這條船上,背景是搖搖欲墜的高聳宮殿。許多往日的伙伴放棄了曾經的強國寄望,只有鄧世昌,雖不能左右國事,卻甘愿舍棄自己的生命,勢要撞沉吉野艦。
從始至終,這是鄧世昌一個人的抗爭。當他沒入沉寂的海底,好似看到了年少時的自己,那時候,父親還在,父親就是他的“致遠”,載著他的夢想,送他學航海、學洋文。直到鄧世昌真的登上致遠艦,看到了耀眼的光亮和中華致遠的希望,父親鼓勵他,建功立業,當在海上。
再后來,就連李鴻章也“年近古稀鬢發斑”“萬千心事萬千山”,鄧世昌在希望泯滅之時想家了,過去20年,他只回過兩次家,再返鄉,父親已經去世,致遠艦也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巡洋艦。
李小萌飾演的水妹子在絕望中給了鄧世昌一束溫暖的光。水妹子身上有女子的柔,有對夫君的仰望,亦有顧全大局的隱忍與剛烈。即便重逢后已有五個月身孕,水妹子依然淚眼婆娑地成全丈夫的選擇。雖然水妹子只是歷史記載中一個語焉不詳的人物,李小萌在其中揉入了眾多她欣賞的女性形象的詮釋,水至柔,亦至善,讓全劇多了一絲柔情。
面對海上無盡的黑暗,鄧世昌劍指長天,永不言敗。電閃雷鳴中,他再次與年少時的自己對話。當致遠艦與吉野艦交戰之時,紗幕降下,鄧世昌舞劍的身影重疊在紗幕之上。“北冥有魚,其名為鯤。鯤之大,不知其幾千里也……”從小誦讀到大的《逍遙游》,是鄧世昌理想世界的外化,這場一個人的戰爭里,他終于可以水擊三千里,扶搖而上九萬里。面對死亡,他無所畏懼。
伴著大氣磅礴的配樂,鄧世昌選擇“一生赴此一戰,成浩然之氣,護佑中華”。一個悲情英雄穩穩立于舞臺之上。在《鄧世昌》中,觀眾不僅可以在戲劇作品感受到英雄之所以能成為英雄的精神高度,更可以觀照自己的生活,努力做出無愧于自己精神追求的個人選擇,或許這就是《鄧世昌》隔著歷史的濤聲演給當代觀眾看的意義所在。
隨便看看:
相關推薦:
網友評論:
推薦使用友言、多說、暢言(需備案后使用)等社會化評論插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