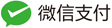這束《暖·光》,照亮不斷變遷的城與人
記者 王筱麗
創作第一部反映上海工人新村題材的舞臺劇《暖·光》,編劇管燕草構思和醞釀了五年之久。三萬字不到的劇本,對她來說既難也不難——她從小生活在工人新村,對這片土地上的點滴故事和溫暖人情再熟悉不過;但要寫好大時代下的新村變遷卻不易,光是劇本修改就經歷了一年。
上海是全國第一個工人新村誕生的城市,以其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和紅色文化是城市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正值上海解放以后首批工人新村落成70周年之際,由楊浦區文化和旅游局出品、上海現代人劇社演出制作的《暖·光》日前在YOUNG劇場首演,以話劇譜寫了一曲工人新村的歌謠。
將工人新村70年變遷“裝”進舞臺
上世紀50年代初的春風拂過大地,為表彰勞動模范與技術骨干,一批工人新村應運而生。《暖·光》講述了張家三代人和師兄李家三代人在建造、擴建、改造工人新村的過程中,從搬入、搬離到再度回歸工人新村的故事。“在似水年華的人生窗欞上,工人新村如同那一抹溫柔的暖光,穿透時間的縫隙,照亮了歲月的臺階。”寫到作品的創作緣起時,管燕草的筆觸充滿溫情。
少年時代,管燕草從石庫門里弄搬進控江新村,“現代化”的氣息撲面而來。彼時石庫門居民大多還過著生煤球爐、倒馬桶的生活,工人新村里則是煤氣灶、抽水馬桶一應俱全。《暖·光》開篇,第一代工人張阿根和妻子從蘇北來到上海,搬進工人新村后止不住地興奮,不停地拖地和擦玻璃,表達對新家的愛不釋手。在管燕草看來,工人新村自帶著一種不同于石庫門和新式住宅的獨有氣質,由于職業、學歷的相似背景,住在這里的人們分享著更緊密的鄰里之情。“誰家家里燒了好菜,會端來一小份給大家嘗嘗。誰家沒空,也會拜托鄰居接小孩時順便把自己的孩子接上。”
對于管燕草來說,將這份濃郁的情感與回憶落成文字并不是第一次。此前,她就曾與父親、著名工人作家管新生合著過三卷本長篇小說《工人》。然而,過往的經驗并不全部適用于這次創作,話劇兩小時左右的常規體量讓她尋找起其他敘事入口,好將工人新村70年的變遷“裝”進舞臺中。
四個時空來回切換,展現溫和淳樸的質感
《暖·光》舞臺場景還原了上世紀50年代第一批工人新村的景象,照理說,工人新村公用空間里每天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故事,這無疑是劇本天然的素材。但在創作過程中,管燕草給自己提出要求,把時代感放在首位,不讓作品顯得過于市井化。《暖·光》中,父親、兒子、孫子三代人皆以28歲風華正茂的模樣登場。上世紀50年代、上世紀80年代、新世紀、當下四個時空來回切換,見證著他們對工人新村欣喜、無奈、懷念各不相同的情感,而時代的流轉亦通過他們的人生一覽無余。可以說,臺上呈現的那一段段故事和劇中人物的生活、命運,也是上海城市發展的一段文脈。
作為曾在工人新村生活足足42年的上海人,著名文藝評論家毛時安認為《暖·光》是一部抒發人文關懷、向共和國“致青春”的話劇作品,“這是一個多少被人們忽略而完全不應該被忽略的創作,真切地表現了中國大地獨有的受益廣大的工人新村的生活”。
《暖·光》落幕,孫子從海外留學歸國,參與了工人新村的改造工程,并為爺爺購置了一套與當年同樣戶型的房子,讓父輩在晚年找到熟悉的歸屬感。劇中的景象是現實中工人新村迭代的縮影,位于楊浦區的“長白一村”就已華麗轉身成為城市新地標“長白228街坊”,這處曾經上海首批完成的“兩萬戶”工人新村繼續肩負著為老百姓所用的使命。
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陳思和在劇中看到了許多微波不驚、卻很有深度的細節,譬如上世紀50年代單位分配住房、上世紀80年代結婚無房、新世紀舊工房改造等等,都成了時代的縮影,讓上了年紀的觀眾看后感到唏噓,讓年輕觀眾看后感動。不追求流量,也沒有太多“燃點”,《暖·光》展現出了一份溫和淳樸的質感,它補上了城市記憶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塊,想講述的正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沉況味。
隨便看看:
相關推薦:
網友評論:
推薦使用友言、多說、暢言(需備案后使用)等社會化評論插件